即便张扬用真实人物自我还原演绎以及置景舞台化打破真实感的方式来贴近人物和从另一层面抒发主角情感,但这些形式上的创新依旧抵不住贾宏声自我本人的魅力,自他一开始直视镜头,那份真诚坦荡的眼神就将自己托付给了观众,正因为这份真诚的存在,才在逐渐还原事件的过程中,愈加糟糕的要求没有激起观众的反感,阻挡对这个人物的进步一思考. 在旁白与真实事态交织的叙述中,贾宏声自我的内心与外界的评价搭造了一个平行的运行轨道,相互对照,又不互相干扰,令观众自我去挖掘内容,正是这一不激起矛盾剧作结构的存在,电影才能在围绕家庭变故的情况下,却始终没有发生情感破裂,贾宏声才能自我的追溯回忆以及反思,最终达到了最后的和解,而这一做法也贯彻了电影一开始就确立的目标——自己.
在旁白与真实事态交织的叙述中,贾宏声自我的内心与外界的评价搭造了一个平行的运行轨道,相互对照,又不互相干扰,令观众自我去挖掘内容,正是这一不激起矛盾剧作结构的存在,电影才能在围绕家庭变故的情况下,却始终没有发生情感破裂,贾宏声才能自我的追溯回忆以及反思,最终达到了最后的和解,而这一做法也贯彻了电影一开始就确立的目标——自己. 但在现实来看,最后和解好似主创们送给他的祝福.
但在现实来看,最后和解好似主创们送给他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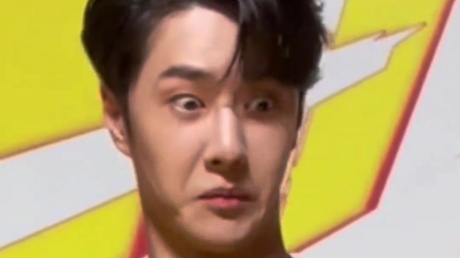 古老的“道路”母题之下的第三世界寓言,充满着大量的隐喻.
古老的“道路”母题之下的第三世界寓言,充满着大量的隐喻. 如果说,在现代性的规划中,教师/知识分子被派定为一个重要的角色——现代文明的启蒙者、文化的播种者,我们将看到在影片中的两位教师反倒更像是某种穿村走巷、沿途叫卖“知识”的“小贩”,并“堕落”成乞食者.
如果说,在现代性的规划中,教师/知识分子被派定为一个重要的角色——现代文明的启蒙者、文化的播种者,我们将看到在影片中的两位教师反倒更像是某种穿村走巷、沿途叫卖“知识”的“小贩”,并“堕落”成乞食者. 另外,除去赛义德临时新房中的一幕,黑板这一负载着现代教育的内涵并充当着现代教育的象征的能指,则无时无刻不充满着荒诞感,呈现在一个不断被转移其功用、丧失其所指的过程之中:担架、掩体、彩礼、离婚赔偿、夹板……如果说教育、教师、黑板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力量和意义,许诺着对愚昧、贫穷中的人们的拯救,那么也正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灾难(两伊战争),毁灭着.
另外,除去赛义德临时新房中的一幕,黑板这一负载着现代教育的内涵并充当着现代教育的象征的能指,则无时无刻不充满着荒诞感,呈现在一个不断被转移其功用、丧失其所指的过程之中:担架、掩体、彩礼、离婚赔偿、夹板……如果说教育、教师、黑板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力量和意义,许诺着对愚昧、贫穷中的人们的拯救,那么也正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灾难(两伊战争),毁灭着. 《热烈》的寓言由此成为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神话极为辛辣的反讽,对现代性话语自身的质询.
《热烈》的寓言由此成为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神话极为辛辣的反讽,对现代性话语自身的质询.